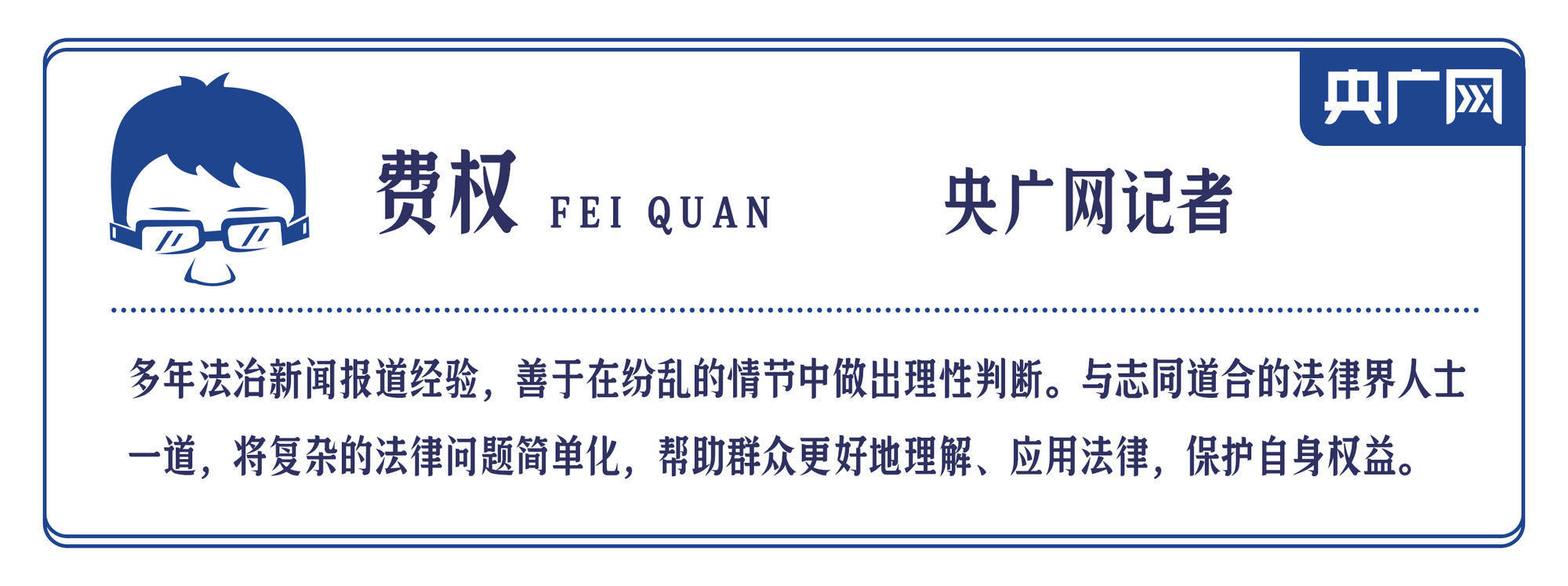央广网北京9月30日消息(记者 费权)“监控里我离老人还有三米远,他自己摔的!”近日,湖南尹先生的善意遭遇成了现实版“农夫与蛇”。他带儿子看病途中扶起摔倒老人,却被家属索赔3万元,还遭“追究刑责”威胁。十余天里,尹先生为自证清白精神恍惚、四处奔波,直到找到隐蔽监控才洗清嫌疑。可面对铁证,对方仅一句“对不起”便离场,其十几天的精神煎熬、经济与名誉损失被轻描淡写。
此类事件并非个例。2025年2月,山东临沂王先生搀扶骑车摔倒的老人后,也被家属诬陷为肇事者,承受无端指责与压力。更无奈的是,两起事件中的讹诈者均未受到实质性惩处,仅口头道歉收尾。这种“低成本讹诈”,让越来越多人在“该不该扶人”的问题上心生动摇——善意被辜负时,付出的代价往往远大于认可。
“‘对不起’三个字,赔不起好人十几天的煎熬。”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徐伟表示,公众觉得讹人“零成本”,是对法律处罚体系的误解。事实上,法律已为“善意”筑起多重保护屏障,讹人者绝非能“法外逍遥”,针对“扶人被讹”的维权路径清晰,可从民事、行政、刑事三个维度为救助者提供全方位保障。
从民事追责来看,尹先生因找监控请假产生的误工费、交通费,及因精神恍惚产生的诊疗费,并非只能自认倒霉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千零二十四条,捏造事实诬告他人构成名誉权侵权,受害人可主张三项赔偿:
一是误工费、交通费等实际财产损失;
二是结合受侵害程度与当地经济水平判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;
三是律师费、取证费等维权合理开支。
值得一提的是,杭州通过地方立法强化对救助者的保护,《杭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》明确,救助人因被诬告产生的费用可全额追偿,且将举证责任倒置给被救助方——无需救助者自证“没撞人”,而需被救助方证明“救助者撞了人”,大幅减轻救助者维权压力。
在行政层面,法律对讹诈行为也有规定。2013年“三儿童扶老太被诬陷案”中,诬陷者之子因虚构事实实施敲诈,被依法行政拘留10天、罚款500元,仅因老人超70岁才依法免于拘留。徐伟解释,此类讹诈行为可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,若存在“索赔+威胁”情节,符合“敲诈勒索”认定;若故意捏造事实诬陷他人,可适用“诬告陷害”条款。以尹先生遭遇的“索赔3万+刑责威胁”为例,即便讹诈者未实际拿到钱,只要实施了威胁勒索行为,即可立案处罚,并非“得手才算违法”。
若讹诈行为进一步升级,还可能触碰刑事法律红线。徐伟介绍,当行为人“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”时,可能触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四十三条“诬告陷害罪”,需满足三个核心条件:一是捏造“故意撞人”等犯罪事实;二是向司法机关告发;三是情节严重(如导致对方被立案侦查)。此外,若索赔过程中使用暴力威胁,可能构成“敲诈勒索罪”,根据相关司法解释,单次勒索3万元已达“数额较大”标准,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。例如,若山东临沂王先生案中,家属向警方诬告王先生“交通肇事”属实,就可能涉嫌诬告陷害罪。
结合尹先生和王先生的经历,徐伟总结了救助者的“善意守护指南”,帮助大家兼顾“助人”与“自保”。
一是遇到老人跌倒,别急着扶起,先观察老人意识、身体状况(如是否有外伤、能否活动),尝试呼救寻找附近专业医疗人士,并立即拨打急救电话——不同身体状况的老人需不同救助方式,盲目搀扶可能加重伤害,专业救助既能保护老人,也能避免后续争议。
二是帮扶时尽量找周边路人共同施救,既能合力为老人提供更周全的帮助,若后续出现“认错肇事者”或“故意讹诈”,第三人也可作为证人佐证,减少纠纷风险。
三是施救前观察周边是否有监控设施,有则记录监控位置以便后续调取;在不侵犯他人隐私的前提下,用手机拍摄现场照片(如老人跌倒位置、周边环境)、录制视频或录音(如与老人、家属的沟通过程),这些材料将成为日后维权的关键证据。
四是一旦遭遇“碰瓷”,别因“怕麻烦”放弃权利,应通过法律途径主张民事赔偿,既能保障自身权益,也能让讹诈者承担后果,避免其继续损害他人善意。
尽管法律规定明确,为何仍有讹诈者能“全身而退”?徐伟指出核心症结:“很多受害者因‘怕麻烦’‘耗不起时间精力’放弃追责,导致违法成本远低于维权成本,间接纵容了讹诈行为。”对此,他提出两点建议:一方面,公安机关遇到此类纠纷应更主动介入,及时固定证据、排查事实,避免因“民事纠纷”定性放任讹诈行为;另一方面,可参照杭州“举证倒置”规则,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减轻救助者的举证压力,让救助者无需为“自证清白”耗费过多精力。
“尹先生们的遭遇,是社会信任的试金石。”徐伟强调,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百八十四条“好人条款”早已明确: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,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。当法律的“惩戒利剑”与“保护屏障”同时发力——让讹诈者付出沉重代价,让好人的善意不再被伤害,才能让“扶不扶”的纠结选择题,变回“敢不敢”的良心题,让更多人愿意在他人危难时,毫无顾虑地伸出援手。